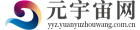今年春节,吐槽长辈催婚的年轻人变少了。
相反,在经历了疫情三年、各种不确定性频繁出现在生活中后,曾经追求自由、独居的年轻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情感生活。
高烧不退时递来一颗退烧药、头晕目眩时有人可以做好一碗热粥、在医院等待时,有人能帮忙挂号付费忙前忙后……
 【资料图】
【资料图】
一场疾病,足以杀死一个人的孤单。
婚恋平台的数据最能证实这一现象,2021年中国互联网婚恋交友市场规模达到72.0亿元,同比增长11.6%。
2022年上半年,互联网婚恋交友用户规模总体呈现平稳增长态势,6月用户规模突破3300万,达3346.9万人。
婚姻,或许带来的不仅仅是束缚、失去自由,也可以得到永远支持自己、帮助自己的伴侣,为不确定的人生增加一分确定。
但如同所有行业,在高速发展的时候,必将伴随无序、野蛮的竞争一样,婚恋交友市场也充满了陷阱。
本期显微故事将走进婚介产业,他们之中:
有的人是支付了天价服务费后,却被红娘反向教育了一番,对方说她“眼界高”,让她“反思自己的择偶观”,从相亲服务变成了“指责服务”;
有的人从事相亲行业红娘职业,她坦白自己就是靠贩卖焦虑实现财富增值,如今成为了行业高收入群体;
在“说媒拉纤”这个古老的行当里,我们会看到行业、城市变化带来的另一面变化。
以下,是关于这个行业的真实故事:
1. 为了找到另一半,花5万元算什么?
赵晴是被小红书“骗”进婚介所的。
29岁的赵晴是出生于湖北县城的独生女,远在上海工作,因社交有限,自2017年分手后赵晴一直处于空窗期。
她也尝试过线上相亲。但因为龙蛇混杂、赵晴一直没有配对成功,以至于她想过“要不就单身算了”,甚至还去网上了解过“单身女性抱团养老项目”。
但2022年充满不确定的生活让赵晴犹豫了。
去年12月,全国放开疫情封控,赵晴也成了第一批“小阳人”。当赵晴发着高烧、浑身酸痛地躺在床上时,她感觉自己就好像“提前体验了老年时不能自理的生活”。
那是赵晴第一次萌生出结婚的冲动,主动上网询问“如何快速脱单”。
她将自己的想法发在网上后,无数“单身俱乐部”的红娘通过社交平台联系到她。
这些账号大多以“单身”、“爱情”冠以账号名称,主页有非常多的“优质男性”资源,个个都有房有车、年收入几十万,“按照择偶范围打造的”。
图 | 赵晴每天都会收到很多“招呼”
添加这些账号为好友后,对方会不约而同寒暄几句,随后就发给赵晴长串的待填项目。
填写完后,对方会打电话邀请赵晴到门店中做个“认证”,言之凿凿保证“自己线下资源、绝无欺骗、可以来了解一下”。
在连续接了5家不同平台的邀约电话后,赵晴终于走进了位于陆家嘴的写字楼里。
如果不是提前预约得知具体位置,很难想象在一众科技公司、金融公司中,夹杂了这样一间“婚介所”:走廊上挂满了锦旗、宽敞的空间被隔成小单间、单间墙上则贴着许多情侣照片。
预约的脱单顾问“冯老师”也变成了另外的爱情导师“黄老师”,认证也没有查看身份证,变成了1v1推销。
图 | 和爱情导师沟通的1v1小房间
在私密小隔间谈话的2个小时里,红娘从赵晴的年龄、工作、家庭出发,给出了“适合结婚,但需要努力才能找到对象”的判断,并给出了28800元和48800元的两个套餐。
图 | 赵晴去的婚介所提供的套餐服务
前者只介绍5个匹配的对象,后者不仅介绍5个对象,提供全程的约会指导,如规定时间内成功恋爱,则退还50%的金额,看起来更具有吸引力。
看赵晴还有些犹豫,红娘马上拿出手机展示了最近一周的收款记录:其中有生活在上海嘉定、02年的护士;也有94年出生、年薪百万的清华博士,一长串的名单滑不到底。
“丫头,02年的都来相亲了,30岁是个门槛,你再不抓住机会,就找不到好对象了”,说罢还向赵晴展示了手中男会员资源。
最终在对方“最快下周能约会”的保证和“高达72%的配对成功率”的历史数据下,赵晴使用花呗缴纳了48800元成为会员。
随后,红娘给赵晴总结了一份“情感报告”,里面用各种专业术语分析了赵晴的不足,并承诺下周就能开始相亲。
图 | 赵晴收到的情感报告
之后赵晴约见了3位对象,但都不如之前在红娘手中看到的男生那般合心意,每次双方尴尬的对坐着,只有一边的老师在努力“拉郎配”。
失败次数多了之后,热络的老师也变得高冷。
原本承诺的“特别好找对象”,变成了赵晴“眼界高、择偶标准畸形、不容易脱单”、至于自己“还要服务其他的客户,没办法做到及时响应”。
等赵晴想要退款时,才发现自己前路漫漫:合同中只约定了见面的次数和服务时间,还有30%违约金,根本无法全额退款。
2. 制造焦虑,红娘销售的“秘密法宝”
赵晴将自己的经历发布到网上,引来了许多有相同经历的年轻人。
其中,有个深圳网友和赵晴说,自己也是在被某个线上婚介平台吸引,“平台上男生都有房有车,收入极高”,付费后红娘推荐了几位,“线上聊着可以、一聊到线下见面就没音信了”。
她找红娘要说法,对方却趁机推荐情感课程、心理课程,让她多学习和异性相处。
“这明显就是下套,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成功配对,把你当猪宰”。
图 | 某婚介所等待客人的红娘
还有个网友和赵晴说,自己也去了某个连锁婚恋品牌的线下门店,付了28800元套餐费,接着就被红娘密集定了好几次约会,“来的人都不怎么样,感觉红娘就是为了快点消耗约会次数”。
甚至还有个网友,在婚介所支付了5万元定金后,还没等服务期到期,婚介所就直接卷款跑路了。
图 | 网友们分享自己被婚介所欺骗的经历
“想要通过婚介所找到对象,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蔡佳说。
87年出生的蔡佳曾经在一家以婚介知名的互联网婚公司工作,做过5年“红娘”,“这个行业并不规范”。
不规范的根源在于盈利模式。
蔡佳解释,婚介所的盈利模式为收取“服务费”,但婚姻本身是非标的,于是服务的考核只能落在“约见次数”等可以具体化的层面上——这才出现了许多钻空子、想要消耗次数尽快完成约见次数的情况。
此外,红娘的收入多采用“低工资+高提成”模式,即成功签单后可以拿用户缴纳金额6%-15%的费用作为提成,所以红娘们更像“销售”。
他们会用各种话术挖掘用户们的信息、然后促进成交,“一旦发现不是目标客户,或者成交后,我们会毫不犹豫撤离”。
为了提高成交,公司会针对红娘培训,包括如何打压用户、3个小时内分别用什么话题来引导聊天节奏等。
红娘们还会去不同平台“盗图”、编造信息,伪装为手上拥有的优质资源;甚至不少平台会雇佣“婚托”来提升用户活跃度。
“最重要的就是制造焦虑,焦虑了对方自然信任你”,蔡佳回忆。
她曾经有个同事接待了一名被父母带来的海归女生,对方32岁,自己创业,年收入能有50万,在上海有房有车,并不着急结婚,相反站在她身边的父母比较急。
同事画了一个时间轴交给她的父母:
“相亲谈恋爱起码得1年吧?到时候过二人世界得一段时间吧?”
“怀孕得一年吧,你现在32岁了,如果再不抓紧就是高龄产妇了。”
“你这个年龄,我不保证能匹配合适。”
父母内心的焦虑被激发,当场交了6万多元,购买了最贵的套餐。
“可以说,制造焦虑是红娘的法宝”,蔡佳回忆,自己曾在一天之内成交5单,光提成就有1万多元。
退款难则是因为婚介行分工越发精细导致的。
53岁的黄文月是一名入行20多年的红娘,“以前我们红娘直面客户”红娘都是公园等地出没,将合适的男女信息登记,然后进行配对,两人出现了问题也是红娘调节,“一般只做熟人、本地人的生意”。
但现在交通、网络发达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流动起来后,情况发生了改变。
“现在年轻人爱上网,都喜欢网上沟通”,黄文月的婚介公司也将网络视为了重点阵地,并配备了不同的工作人员,即先由账号运营人员在不同平台上发布信息“养号”,有用户互动、留言之后私信对方获取联系方式。
“我们还去同行的帖子下联系潜在用户,然后获得对方联系方式后交给‘电邀红娘’(又称为脱单老师等),电邀红娘和用户进行初步的沟通后,邀请至店里,再由面谈红娘促单。”
环节中的每一个岗位考核都不同,比如联络员,一旦成功联系一个用户就有提成,“都需要成本,所以不可能全部退款”。
另一方面,面谈需要场所,而大部分的婚介中心需要用户到店面谈,要考虑交通,所以大多开在市中心的写字楼里,成本昂贵。
图 | 赵晴去的婚介所就在这栋写字楼中
“说到底,我们都是在做生意,只是交易的对象是人”,蔡佳戏谑道。
3. 一个被“高速发展”劝退的行业
在维权的过程中,赵晴发现一个特殊的现象:许多高达万元的相亲维权里,女性比例高居不下,“甚至只有女性”。
“这是大城市相亲市场里男少女多造成的”,蔡佳说。
一般相亲服务费和当地收入水平相关,能付得起数万元相亲服务费的群体大多聚集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
这些城市因房价高、生活成本昂贵,许多经济能力稍逊色的男性被拦在了相亲市场门槛之外,以至于出现了女多男少的情况。
这也导致了适婚、有一定基础的男性成为稀缺资源,因此大城市中的女性成为相亲付费的主要买单方。
在男女“供需”端不平衡之下,婚恋交友市场迎来巨大发展。
比达咨询2022年1月6日发布《2021年度中国互联网婚恋交友市场研究报告》(简称“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互联网婚恋交友市场规模达到72.0亿元,同比增长11.6%。
但现在,这个“人口”生意并不好做了。
曾经女多男少的优势,反而成了劣势。和其他服务不一样,婚介服务属于低频次的服务,“很多人只会购买一次”,而男性资源的缺乏,使得配对成功率下降。
为了维持销量,曾经不少公司采用婚托、编纂虚假信息吸引用户,“但很多用户了解到真实情况后就不再上当”。
作为电邀红娘的李菲明显感觉到用户产生了抵触心理,“有时候我们刚说出自己是‘情感老师’对方就挂断了。”
和李菲搭档、负责运营公司账号、发布征婚信息、收集女性用户信息的王肖也觉得“难”做了。
2021年她刚接手公司账户时,评论区还有许多人友善留言、点评发布信息的用户,或者私下给自己发送消息询问情况:
“今年则很多用户在评论区骂我们是骗子”,并劝阻很多留言用户“别相信”,甚至会自发举报账号。
仅去年下半年,公司就有7个账号被封。
另一边,疫情催生了一批“想结婚”的年轻人,也带来了许多不确定——很多被裁员的适龄年轻人,就此选择了回到家乡或者省会。
黄文月最近打电话时感触特别深,“好多女孩子联系着联系着,就发现回老家了”,而回到老家或者省会城市的年轻人,“或多或少都有亲戚在身边张罗,不需要婚介”。
留下来的年轻人择偶观也发生了改变,“以往程序员是香饽饽”,李菲说现在很多女孩子会强调工作稳定、经济条件好,“可哪有这么多实力雄厚的男生?”
于是行业只能押宝在销售上,“那不又回到了虚假营销上面?”
可高昂的服务费用劝退了不少年轻人,“毕竟年轻人也越来越没钱了”;此外,一线城市的房价高昂,越来越多“不婚”的声音出现,也让李菲、黄文月、王肖等从业人士感到行业难以持续。
来自年轻人的反击更是削弱了婚介的市场——很多年轻人抱团成立了社群,不收取服务费,通过线下活动来撮合单身;甚至不少公司为了留住人才,开始倡导联谊、解决男女青年的婚姻问题。
在对未来的不明朗之下,蔡佳选择了离开,“我们就是销售,谁也不知道这个行业还能做多久”。
制造焦虑,曾经是行业人士的成交法宝。但现在,“焦虑”也成了挂在婚恋行业从业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