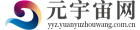在上世纪初到50年代的美国,还有后来的一些新兴国家,关于城市建设都有一种论调:“只要我有足够多的钱,就能把城市建设好”,也就是俗称的“大气魄和大手笔”。
它主要依托于西方世界自20世纪以来的一系列空间规划和设计方法论,包括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柯布西耶的“光明城市”理论,以及始于19世纪90年代流行于北美各大城市的城市美化运动。这些理论并非一致,柯布西耶对城市功能区的划分、对效率的极致追求,就是对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的颠覆。但总体来说,它们有着“大气魄和大手笔”的共通性。
纽约就是例子,它曾倡导城市郊区化和建筑现代主义化,着力建造城市地标。它以“摊大饼”的模式扩大城市规模,然后为了加强区域间联系,开始修建复杂的交通网络。
 (资料图)
(资料图)
拥有巨大隐形权力、主宰纽约城市重建的罗伯特·摩西就满足了许多人对“魄力”二字的错误想象。他沉迷于摩天大楼和高速公路,以“拆拆拆”方式切除所谓的“城市癌变组织”,疯狂清理贫民窟,消灭无数街区。
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里,简·雅各布斯将摩西式的想法乃至霍华德、柯布西耶等人的理论讥讽为“一厢情愿的神话”。认为他们不是从理解城市功能和解决城市问题出发,来规划设计一个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反而或是以“反城市”的“田园”为目标(如霍华德),或是用假想的乌托邦模式(如柯布西耶),来实现整齐划一、非人性、标准化、分工明确、功能单一的所谓理想城市,并对违背这一模式的街区进行残酷清理。“这不是城市的改建,这是对城市的洗劫。”
城市建设从不是电脑游戏。在《模拟城市》之类的游戏里,玩家可以建造一座梦幻城市,而在现实中,每座城市都必须面对真实的人。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所倡导的,正是城市规划背后的人文精神。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60周年致敬版)[加拿大]简·雅各布斯/ 著,金衡山/译,译林出版社,2020年7月
1916年,简·雅各布斯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1952年任《建筑论坛》助理编辑。在负责报道城市重建计划的过程中,她逐渐对传统的城市规划观念发生了怀疑,认为美国大城市正面临某种灾难,并于1961年写作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
在她看来,城市活力来源于多样性,城市规划的目的在于催生和协调多种功用来满足不同人的多样而复杂的需求。正是那些远离城市真实生活的城市规划理论、乌托邦的城市模式和机械的、单一功能导向的城市改造工程,毁掉了城市的多样性,扼杀了城市活力。
这本书激怒了当时的美国城市规划者们,认为简·雅各布斯不过是妇人之见。可历史证明,正是简·雅各布斯的理念改变了美国的城市建设。
但,城市规划是一个“永无终点”的项目,它也受制于太多因素。时至今日,简·雅各布斯的理想城市仍未真正出现,各种新问题却层出不穷。
《杀死一座城市:缙绅化、不平等与街区中的战斗》[美]彼得·莫斯科维茨 / 著,吴比娜 赖彦如 / 译,理想国|山西教育出版社,2022年7月
彼得·莫斯科维茨在《杀死一座城市:缙绅化、不平等与街区中的战斗》中写道,缙绅化为城市带来金钱、新的居民、整建后的房地产,但同时也摧毁了城市。它抹杀了简·雅各布布斯最看重的多样性,城市因此难以孕育独特、大胆的文化。
所谓缙绅化,即指房租不断上涨、连锁品牌入驻、熟悉的面孔越来越少、在地文化逐渐消失。旧社区重建后,地价及租金上升,吸引高收入人群迁入,原有的低收入者则不得不迁走,这就导致了缙绅化进程一再深入,也让城市距离活力和公正越来越远。
二、五十年后的西村发生了什么?
简·雅各布斯与彼得·莫斯科维茨对城市的研究相隔五十年,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研究对象——纽约西村。
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雅各布斯曾探讨纽约西村的魅力,以此印证当时主流城市规划观念的错误。当时的西村,拥有小而有多样的街道景观,多种职业、阶级与种族的居民,多样的文化,在杂乱中迸发出强大生命力。
彼得·莫斯科维茨将自己视为雅各布斯书中的角色之一,他在西村长大,“十岁的时候,能够自己一个人走路到哈德逊街的小学,因为路上的人我都认识,爸妈根本不必担心。”
但50年后,当莫斯科维茨大学毕业回到纽约,发现西村已面目全非,充满童年回忆的建筑被推倒、重建,取而代之的是闻所未闻的财富象征,天价房租迫使他搬离西村……
莫斯科维茨忍不住提问:“一度昭示着多元平等,成为最佳楷模的西村,如今变成全美最昂贵、纽约族群最单一的社区,这对美国城市的未来意味着什么?而那些被迫离开这个新的西村的人们,他们又怎样了呢?”
于是,便有了致敬《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杀死一座城市》。彼得·莫斯科维茨试图以美国四座大都市——新奥尔良、底特律、旧金山、纽约——为例,逐一分析其城市格局与人口结构的变迁根源所在。政府与财团的共同规划,使城市更有利于资本的累积而不利于穷人生存。
对于一般的纽约人来说,西村的变化仅仅是“酷”与“不酷”的区别,但对于简·雅各布斯来说,西村这类地方的存在,证明城市可以不需政府干预而自我运转,无须太多外力帮助就可达到平衡。她认为“小店家、吸引艺术家和作家的便宜租金、长短不一的街廓,以及多用途混合的分区政策,让西村的街道成为观看人来人往的好地方,也让社区成为一个亲密的系统……多样性的建筑,从高级华厦到旧出租屋,意味着一群多样的人可以负担不同的租金从而入住同一个社区,不会因为收入多寡、族裔背景而被区隔。”
缙绅化则将这些街区推向另一个方向:老居民搬走、在地文化消失、财富和白人开始涌入纽约小区。“对纽约的穷人来说,缙绅化不是一种社区特质无形的改变,而是他们真切面对的群体驱逐、金权暴力,还有悠久在地文化的铲除。”
三、缙绅化是城市的系统暴力
《杀死一座城市》中写道:“缙绅化不只是一种时尚或潮流。嬉皮士和雅皮士们比起被他们驱离的老居民财力更强,但个别的行动者没有能力控制房屋市场,凭一己之力改变城市。缙绅化也无法由个别投资者行为来解释:在新奥尔良拥有五栋房子的房东跟底特律的公寓主并没有彼此商量策略。缙绅化下有胜利者也有受害者,双方都在同一场游戏里,尽管他们都不是游戏的设计者。”
换言之,缙绅化并不是个体行为,也不是某个阶层的独立行为,彼得·莫斯科维茨将之视为城市的系统暴力。
《不平衡发展:自然、资本和空间的生产》[美]尼尔·史密斯/著,刘怀玉 付清松 / 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5月
1979年,《不平衡发展——自然、资本和空间的生产》一书的作者尼尔·史密斯提出了对于缙绅化可能最具影响力的学术观点:租隙理论。他认为过往越缺乏投资的空间,在缙绅化时越能够获取利润。当然,这一点立足于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资本会流向有最高获利回报、获利可能的地方。
对于城市而言,租隙理论和缙绅化的最大后果在于它被变成一个企业。城市必须要更有“商业精神”,城市规划者要更像“经理人”,城市也会像企业一样,以“盈利”为第一目标。
在莫斯科维茨看来,这正应了简·雅各布斯的箴言:“要把一个地方变得单调、贫瘠、粗鄙,天价资金、机关算尽和公共政策,三者缺一不可。”
缙绅化是每个工业化国家都会面临的问题,但严重程度不一。在缺乏完善住宅法规的国家,缙绅化才会造成大规模的被迫迁移和生存危机,美国就是例子。德国和瑞典等国家的情况好得多,这是因为这些国家意识到完全私人主导的土地市场无法满足穷人需求,因此采取各种手段,至少将一部分土地保留于市场机制之外,通过法规限制让人们能够负担其价格。
但美国社会显然无法意识到这一点,“在美国,每年都有1万户受补助的租屋单元消失。美国对于穷人的住宅政策,大多数都是零星而随机,没有经过缜密的计划,也从来不是以成长为导向的市政府、州政府的首要目标。”
对于先发国家来说,城建发展较早,城市重建的难度也比后发国家要大得多。因此,天灾往往成为缙绅化的契机。
2005年,卡特琳娜飓风给新奥尔良带来了灾难性破坏,之后便是重建。但也正是“重建”,让这座城市的气质面目全非。新奥尔良曾是美国最多样化、最有趣的城市之一,多元文化、语言和各种建筑风格并存,也是黑人爵士乐的发源地,但重建让这一切都不幸消失。
重建中的公共舆论是冷酷的。时任州长凯瑟琳·布兰科说要“用一生的风暴来创造一生的机会。”一位房地产投资者表示“我们不希望暴风雨前的人回到这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在飓风发生一周后的文章中说:“如果允许人们回来,新奥尔良将再次成为犯罪猖獗的贫穷城市,我们为什么要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这些言论与政策制定者的思路是一致的。
飓风后重建的新奥尔良,公共住房项目基本关闭,私人住房取而代之。开发商重塑了社区的形貌,使之以白人为主,利润更为丰厚。如今,这座城市已恢复到卡特里娜飓风前的人口,但黑人居民比风暴前减少了十万人,千篇一律的连锁品牌入驻,充满人情味的多元社区日渐衰落。如今的新奥尔良,已经完全专注于经济增长,不再修复或回顾卡特琳娜带来的伤痛。
但如果将缙绅化归结为私人资本的进入,那就非常片面。缙绅化的无处不在,更多是因为一个足以影响政策的角色——政府。过去半个世纪,联邦政府一再削减社会住宅、社会福利、公共交通的预算,城市只能自力更生,依靠自身税收去承担基础服务。这使得城市政府只能鼓励商业和产业发展,吸引高收入或中高收入的家庭移入城市。也就是说,城市必须要尽全力吸纳那些有钱和中上阶级的居民,以这部分群体的税金和购买力为倚仗,解决财务缺口。
对于大多数美国城市,乃至世界上的许多城市来说,发展中的问题解决起来都复杂而困难,缙绅化却是一个简单直接轻松的选择。纽约前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就曾提出:“如果我们能再让几个亿万富翁住在纽约,我们的许多问题都会得到解决。”但这也是饮鸩止渴的做法。
四、简·雅各布斯构想的城市能否重现
简·雅各布斯对城市和街区的构想,或许确实有不合时宜的一面,但仍然是许多人所憧憬的。
她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写道,老城市和老街区虽然看起来缺乏秩序,但实际上背后却有神奇的秩序在维持着街道的安全和城市的自由。同时,它也会带来真正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真正体现城市文明,“让互不相识的人能够在文明的、带有基本的尊严和保持本色的基础上平安地相处。”
城市建设就像一个巨大的实验室,难免会有错误与失败,但也提供了学习的契机。可惜的是,城市建设的实践者们却往往忽视了那些失败,仅仅遵循于一些表象原则和大而化之的概念。
缙绅化的受害者并不仅仅是贫民,当一个阶层被驱赶,意味着会有另一个阶层变成新的城市底层。“如果城市是一架梯子,缙绅化把每个人都往下推了一级,最弱势的人被彻底地推下去,中产阶级则落到底层,甚至有钱人也会感受到来自上层的压力。”
“只有那些完全不依赖政府服务的人——那些有私人交通工具、负担得起私立学校学费、有足够资金购买房产或承受租金涨幅的人,才能漂浮在缙绅化掀起的海浪之上。”更糟糕的是,即使是这部分“幸存者”,也必须面对缙绅化导致的无聊城市。
彼得·莫斯科维茨在《杀死一座城市》中给出了几种解决方案:“借由政府拥有土地兴建公共住宅,或立法采取严格的管制,控制租金或土地价格上扬,或是我们可以通过住宅补贴这类政策,防止攀升的土地价格致使人民迫迁。”
不过在目前情况下,人们似乎只能期盼市场力量能自行解决问题。若没有重大法规革新,那么在可见的未来,城市的中心将越来越具吸引力,穷人将被流放到郊区,直到城市与郊区的租隙降低,缙绅化无利可图,才会又开始新一波的空间重组。
将一切交给时间,或许是无奈又可行的方法。就如雅各布斯所说:“单调且缺乏活力的城市只能是孕育自我毁灭的种子。但是,充满活力,多样化和用途集中的城市孕育的则是自我再生的种子,即使有些问题和需求超出了城市的限度,它们也有足够的力量延续这种再生能力并最终解决那些问题和需求。”
但愿如此。